在铺天盖地的禁毒信息中,其中有一个案例给予我很深的感触。案件讲述一名年约30岁的年轻小伙子王某为了给母亲凑够医疗费,不惜冒险人体运毒,最终被法院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些年,毒品犯罪集团以高价诱惑年轻人冒险帮其运毒的案例屡见不鲜,看似这起案件与以往的案例没有特别之处,实则不然。老母亲年纪尚大,身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昂贵的医药费给家庭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父亲背负不了沉重的生活压力而选择离家出走,小伙子为了救母,一人做两份工作,尽管很勤奋,工作很努力,但所赚的工钱依然无法让其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直至某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则高薪招聘广告,为了凑足费用,王某动了心思,选择只身一人来到云南,但到后发现,工作的内容竟是人体运毒,此时的王某追悔莫及,在毒品犯罪团伙的要挟、强迫及利诱下,王某吞下了84粒毒品胶囊,根据对方的指令,从云南人体运毒至北京。王某被抓后,从其体内排出的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共计300多克。与其他毒品犯罪案件不同的是,王某被抓后就坦白所有的犯罪事实。鉴于其认罪认罚,且系初犯、偶犯,检察人员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便给予15年的确定量刑建议。开庭审理接结束之时,审判长让王某转身面向旁听席,王某与前来旁听的老父亲面对面,泣不成声,而面前的老父亲老泪纵横,悔疚地重复道“都是我的错。”场面让人感慨万千。
我们常说法律是冰冷的,而司法是有温度的。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就运输300多克冰毒或海洛因的涉毒人员而言,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刑期是无期徒刑,检察机关给王某的量刑建议已是最低的法定刑。这是官方曾发布的一则案例,无论是从人伦道德,还是从法律适用,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如王某对母亲的孝顺,司法人员基于全案的情节,对王某适用了法定刑幅度内的最低处罚,但上述案例也引发了我对类似案件的思考。
这些年,毒品犯罪集团以高价诱惑年轻人冒险帮其运毒的案例屡见不鲜,背后的毒枭为了减低自己被发现的风险,在网络上发布高价招聘雇员的启示,以高额利诱无知的年轻人帮忙运输毒品,在这些被捕的运毒“骡子”中不乏有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未成年学生、高校大学生及因赌博而欠债的社会青年等,他们迫于各种原因急要获取一笔钱来填补自己的财务漏洞,焦头烂额地寻找解决之法,而恰好又在网络上看到如此诱人的“工作”,不禁动了心思,都不知自己已经中了圈套。幕后毒枭帮他们买好了机票,一步一步引领他们通过非法途径到了国外,等他们发现对方原来要求自己人体运毒时,却为时已晚,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了说不的权利。对于这类案件,对这类被追诉人是否应当可以作最低的刑事处罚。甚至,是否可以作免除处罚或作无罪处理呢?这个是值得探讨的。
其一,从胁从犯的角度来看,应从宽处理。他们在浏览招聘广告、在出发前往国外之时是未认识到工作内容是运输毒品的,主观上是无帮助他人运输毒品的故意。在吞下毒品之时,人身自由又是被控制的,手机、电话等所有的通讯工具均被没收,完全阻断了他对外求救的途径,稍有不服从,面临的就是暴力殴打乃至被杀害灭口。简言之,他们的主观恶性极低,且是被胁从参与毒品犯罪,在法律上应当是胁从犯。刑法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其二,对具有特殊情节的个案是否能够启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小伙子心切救母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分别发生在广州与北京的两个案件。2009年,张氏兄弟为救身患恶疾的母亲,在广州三元里的街头用菜刀劫持一名女子,只求索要赎金2万元。该案引起了法学界对张氏兄弟涉案行为之定性及量刑的争论,究竟构成抢劫罪还是绑架罪,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又该如何量刑?轻判不足以体现刑法的威慑力,重判不足以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深入的探讨,广州白云区法院一审判处张氏兄弟犯绑架罪,哥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弟弟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2012年北京男子廖丹为了让患有尿毒症的妻子完成透析,私刻医院公章,伪造收费单,四年时间里骗取17余万元,这个“北京爱情故事”案发后,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除了对医疗体制抨击外,更多的聚焦于法院如何衡量法律与人情,最终法院认定廖丹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让廖丹得以在家中照顾妻子。
回归到王某人体运毒救母的案例,是否会有旁观者认为刑期依然太高。笔者不是站在辩方立场对该事提出评论,也不是出于一个法律人的视野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是基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朴素正义感提出的内心最真切的想法。同时,我也不是对司法机关的断案量刑批判,而恰好是认同办案人员的司法良知,但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若在监狱内表现良好,能获得不错的减刑,也可能要服刑八九年,这就意味着他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最值得奋斗的时光都是在铁窗内度过,我们不禁会敲问真的有必要关他那么久吗?之所以觉得量刑太高,是我们得寸进尺吗?
刑法第六十三“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刑法规定了有些特殊个案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以寻求罪责刑相适应,做到量刑公平、公正,真正地罚当其罪,但这个条文几乎已被司法人员闲置了,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刑的程序太复杂了,很多司法人员也不想“多此一举”。对于类似于王某这样的特殊个案是否能够启动这项程序呢?我想这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其三,从违法阻却事由上来看,他们可符合紧急避险的规定。刑法第二十一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在自由被毒枭限制与控制,在人身遭受殴打甚至杀害的危险时,被迫而选择吞下毒品,然后按照毒枭要求,人体运毒到指定地方,实际上是采用了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方式实现保护自身安全及自由之目的,以牺牲低法益保护更高的法益,理应成立紧急避险。但如今紧急避险在司法实务中就成了一个具文,鲜有发现其被适用的痕迹,而同为违法阻却事由的正当防卫在于欢案、昆山龙哥被反杀案中已被激活,所以,如何进一步也把紧急避险也激活,如何在这些被骗运毒“骡子”身上适用就非常值得思考。
其四,从理论上来说,司法人员对这些特殊的运毒“骡子”最大程度减轻、从轻处罚恰好能够实现刑罚之目的。“因为有犯罪,所以有刑罚”,刑罚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在于报复,但这里的报复不同于古代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依据法律规定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行为人报复。对于毒品犯罪,不少人坚持“威慑论”或奉行“重刑主义”,认为乱世就该用重典,严刑竣法,否则无法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国内毒品犯罪高发,涉毒人员猖獗,对涉毒人员就该严厉打击,从重适用刑罚,为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或冰毒在50克以上,就可以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从最高法公布的案例中,常被核准死刑的二个犯罪类型,一是故意杀人罪,二是毒品犯罪。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相比,毒品犯罪中没有被害人。学界很多教授在讨论刑法是否非得让涉毒人员非死不可,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诸多罪名的死刑规定的做法也在启发我国刑法规定的刑期在总体上由重至轻。事实上,奉行重刑主义,并不必然能够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修复社会关系之目的。刑法提供一张“价目表”,规定了行为人实施了某行为,就应当接受某种处罚,许多人涉毒人员并非不知道一旦被抓就很有可能被处以极刑,而是知道后任然为之,他们敢于一而再,而在三地铤而走险,恰恰是知道自己之前的贩卖或制造的毒品数量足以达到被判处死刑的标准,既然横竖均是一死,为什么不多卖些或多生产一些,多赚些钱,恰好能够“牺牲一人,养活全家”,由此引起后续的多次涉毒行为。
相比于上述的“报应论”,现代刑法应更侧重于“预防论”。“为了没有犯罪,所以有刑罚”之所以要对行为人科以刑罚,是为了以后没有犯罪,刑法通过刑罚以达到预防犯罪之目的。“预防犯罪”可以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所谓的“一般预防”可以通俗理解为“杀鸡给猴看”,通过对某个人或某类人的惩罚,达到对社会普通群众的法律教育,警示潜在的犯罪人不要做违法犯罪之事。我们经常在古代剧中看到的官府对某人将要执行刑罚时,通常先把人绑起来,然后关押在囚车当众游街,让老百姓扔臭鸡蛋、青菜,在砍头时,也把行刑的地方选在闹市,其背后之目的也在于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则是预防某个行为人再次犯罪,它不是针对一般个体,而是针对特殊个体。通过将其关押,让其失去人身自由,通过罚款、没收财产,以剥夺其再次犯罪的能力;通过强迫其接受劳动改造,接受文化教育,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同时也掌握一定的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重返社会以后具有自谋生活的能力;通过让其遭受失去自由的痛苦,让其心弃旧图新、重新做人,不再以身试法。
相对于失去生命的被害人,再次剥夺行为人的生命,除了能够平息被害人家属的内心愤怒,再无其他意义,它不能给行为人改过自身的机会,不能给活着的人铺设一条救赎之路,刑罚之目的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救赎,我们绝不能以多杀、重刑为乐。
回归到王某的案件,小伙子本身是初犯,因母亲身患重病而使生活的绝境,在毒枭的要挟之下而被迫人体运毒,究其主观恶性而言,甚至比一般的盗窃、抢劫还要轻,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没有必要将王某科以重刑,若家庭确实没有困难,其也不会误入歧途,若将其关押一段时间,其也不会再次铤而走险。其次,从一般预防或者威胁论的角度,王某的案例似乎更多的不是警示我们不要去运毒、贩毒,而给我们的直接感受是孝心值得称赞,被判入刑让人同情与怜悯。
总而言之,在当前毒品犯罪泛滥的形势下,国家应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但对某些特殊的个案应作区别对待。对具有特殊情节的运毒“骡子”,能否最大程度减轻处罚,体现出司法温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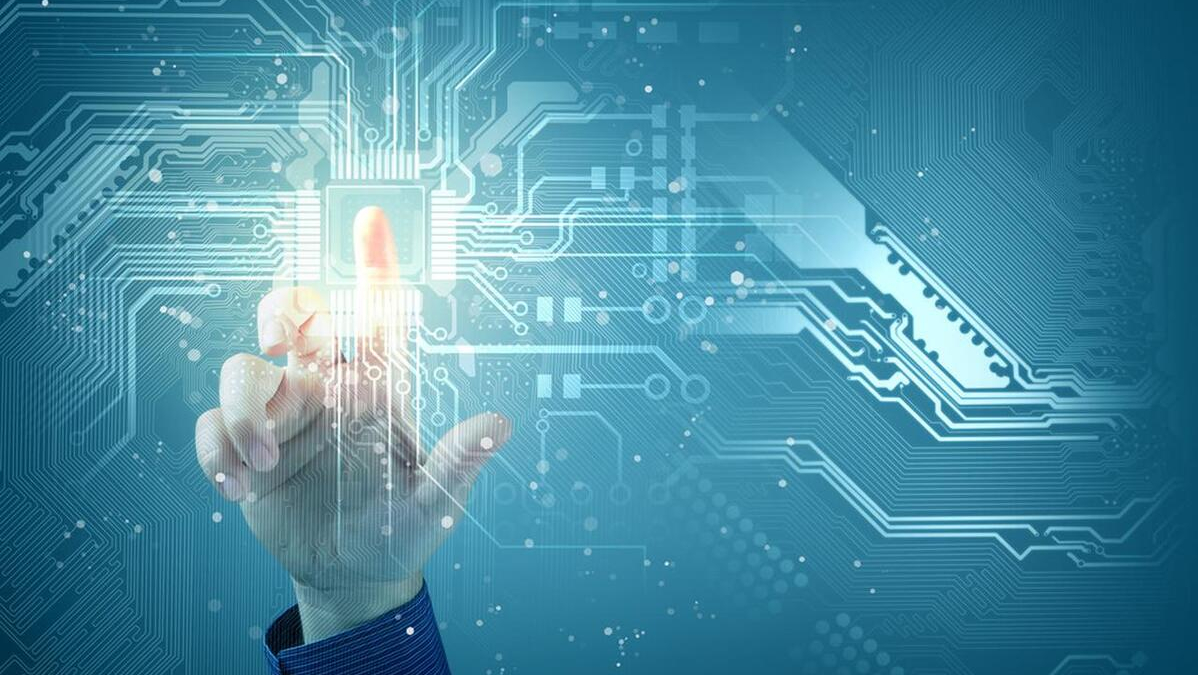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