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现行法的质量标准是“客观职守型援助”,而更高的要求是“合理有效性援助”。以D县为个案,通过与委托辩护律师的对比研究发现,指定辩护实践存在“作用阶梯”现象。从定量角度分析,指定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表现明显不如委托辩护律师,后者相对积极;指定辩护律师在案件定性方面作用不大,较之委托辩护略有不如。而从司法人员的评价出发,指定辩护律师发挥的整体作用也不及委托辩护律师。究其原因,指定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时间过晚、刑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充分、指定辩护质量监控机制偏于形式化是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加强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提高其辩护效果,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内、外因素的调整与变化。此外,确立适当的改革目标也是不可或缺。
关键词:指定辩护 委托辩护 客观职守型援助合理有效性援助作用阶梯
一、导论
(一)概念性框架:“客观职守型援助”与“合理有效性援助”
现代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委托律师辩护,另一种是刑事法律援助。后一来源的主体即是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委托辩护权由被告人自由行使,而指定辩护权首先与案件的严重性,进而与被告人的经济贫困状况紧密相关。[1]从产生背景看,指定辩护制度是平等权利和正当程序主张的必然要求。从程序平等角度,任何被告人,尤其是经济贫困的被告人都应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而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律师辩护应最大限度地避免无辜者被错误定罪并促进公正审判。[1]诉讼实践中,如果没有指定律师的帮助,相当比例的被告人将无法为自己进行有效辩解,更不可能抗制机关的指控、调查与质证。这意味着,从控辩平衡和程序公正角度,国家不仅仅要为适格的被告人提供免费的律师援助,还应当提供合格的辩护律师。
这就涉及指定辩护的最低质量标准问题。理想状态下,从权利保障需要角度,指定辩护应与委托辩护作用相当,适用统一的律师辩护质量标准。在我国,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指定辩护律师必须为受授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2]至于标准为何,则不够明确。综合已有的法律、法规,可以将指定辩护的质量标准大致概括为“客观职守型援助”。它包括“客观辩护”与“职守辩护”两方面的要求。客观辩护是指,辩护律师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其法律依据是第35条、律师法第31条。职守辩护是指,辩护律师应当尽职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其制度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21条。上述两项要求各有侧重,前者指向客观的辩护过程,既适用于指定辩护,也适用于委托辩护;而后者强调辩护律师应遵守作为政府委派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主要适用于指定辩护。可见,在现行法框架内,如果仅考虑辩护过程,指定辩护的质量标准与委托辩护没有区别。由于指定辩护律师具有政府工作人员或者接受政府指派人员的职业身份,因此,对其的职业道德要求更多是一种政府管理机制,与客观辩护并不矛盾。
在美国,无论是委托辩护还是指定辩护,都适用于“合理的有效性帮助”(Reasonably Effective Assistance)标准。早在Powell v. Alabama(1932)案中,最高法院即指出,指定辩护人如委托辩护一样,也必须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3]此后,在McMann v. Richardson(1970)案中,最高法院进一步认为,被告人有权“在的能力限度之内”,获得“合理的合格”的建议。[4]上述判决促使下级法院运用更高的标准去审查辩护律师的能力。自此,无论是联邦还是州的法院,均采纳了更加严格的标准以要求律师按照McMann案的标准执行或者提供“合理的有效帮助”,其具体的职责要求包括:调查所有重要的事实,较高频度地会见当事人,以及询问所有潜在的。[2]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州曾区分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适用不同的有效辩护标准。例如,德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在传统上对待指定辩护与委托采用的是一种“分叉审查”的标准:指定辩护适用“合理有效性标准”,而委托辩护审查的重点则为是否存在“当事人不注意时或者违反法律责任的不当行为”。这种标准经由Ex Parte Ewing(1977)案加以确认。[5]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即推断了上述标准。在Cuyler v. Sullivan(1980)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州法院进行刑事审判时应当遵守第十四修正案的目标,因此,所有法院必须运用同样的标准审查无效性抗辩,而不能区分是指定辩护还是委托辩护。[6]有效辩护标准最终演变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1990年9月,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6条强调,“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的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付费用,可不交费。”
如上所述,尽管现代刑事诉讼对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的质量要求相当,但在实践中,它们有其不同的顾客关系与律师来源,这很可能导致律师作用的发挥程度会有所不同。顾客关系方面,指定辩护源于法院指定或政府委派,律师与政府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而委托辩护基于被告人或其亲属与律师之间的契约。在指定辩护的“顾客关系”中,辩护律师直接服务于被告人,但其最终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委托辩护的“顾客关系”中,辩护律师应忠诚于被告人的个人利益。相比指定辩护,委托辩护的“顾客关系”更加密切。律师来源方面,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有着“大众消费”与“奢侈消费”的区别。申言之,法院或政府提供的指定辩护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具有“批量供应”的特征;与此不同,委托辩护是被告人及其亲属基于市场考察、质量比较,进而通过自愿、平等的交易而产生,具有“个别化服务”的特征。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为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设定完全相同的质量标准显然过于理想化。按照上述逻辑,指定辩护的实际效果在整体上很可能不如委托辩护,但无论如何,都应满足公正审判的底线要求。
(二)中国问题与既往研究
在我国,指定辩护制度最早由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在性质上属于“任意辩护”范畴。[7]1979年《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强制辩护制度,但范围较窄。[8]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指定辩护范围,[9]相应地,1996年出台的律师法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形成指定辩护制度的有力支撑。近三十年来,指定辩护或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不断增长。在1986年,全国法院指定辩护案件仅有9944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8%,占当年所有律师辩护案件总量的7.2%;而至2007年,指定辩护案件增至118946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上升到12.7%,占当年律师辩护案件24.0%。[10]上述数据表明,指定辩护在刑事辩护制度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尽管如此,对于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发挥程度,官方与民间看法相去甚远。总体而言,官方认为,指定辩护整体效果较好,而学者们多认为其作用相当有限。
对于指定辩护作用,司法部采用“辩护意见采纳率”作为统计指标。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辩护意见被全部采纳、部分采纳和未采纳的三项分别占36%、45%和19%,全部采纳和部分采纳合计81%;[3]而到2008年,辩护意见被全部采纳和部分采纳比例上升到91%。[4]如果上述数据属实,指定辩护效果可谓相当显著。而由结果推诸过程,可以认为指定辩护律师在会见、调查取证、庭审辩护方面作用较大。
北京市律协的一个课题组于2002年7月在北京地区的调研采用了“辩护意见采纳率”、“会见率”和“取证率”作为评估指标。在辩护意见采纳方面,无罪辩护的成功率虽然比较高(94%),但和刑事案件总数相比数量却微乎其微(5%);作罪轻或减免刑罚辩护的案件虽然比例比较大(69%),但成功率却不高(43%)。会见方面, 58.7%的律师全部会见过被告人,有些律师只是部分会见或者压根没有会见过被告人,只有9.8%的律师经常会见被告人。调查取证方面,所有案件都进行调查的只有12.4%,完全没有调查、基本没有调查和很少调查的合占72.2%。[5]相比上述调查,李宝岳和孙洪坤的调查结论更加消极。李宝岳负责的调研小组于2004年7月在云南四个地区进行的调查发现,援助律师基本上无力调查取证,一般都会见了被告人,阅卷权受到一定限制。[6]孙洪坤于2005年在安徽淮北市法律援助中心、中级法院进行了调研,访谈中,相当比例的法官、律师认为指定辩护的质量不高,对案件处理影响不大。[7]
从方法上看,司法部的数据源于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上报信息,而地方机构的统计采用办案律师自由填写方式,不排除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为了突出辩护效果而夸大填写的可能性。相对而言,其他三项民间调查由中立的学者亲自进行,尽管数据来源不完整,但可信度较高。这三项研究揭示的共同问题是,指定辩护或援助律师在刑事审判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如果按“客观职守型援助”标准加以衡量,相当比例的指定辩护并不符合要求。何以如此?三项研究揭示的原因主要有:援助律师介入诉讼时间过晚,办案经费不足,援助律师的责任心不够,法院对刑事法律援助不够重视。[11]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材料
以指定辩护律师作用为主题,以“客观职守型援助”为理论视角,本文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继续与深化。本文将系统地回答如下问题: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指定辩护律师在刑事审判中发挥的作用如何?具体表现怎样?哪些因素制约了其辩护效果?以提高指定辩护效果为目标,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近期或远期可如何应对?本文将采用系统、实证的方法展开研究。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以委托辩护为参照,得出的结论偏重于现实主义;而既有研究将指定辩护的实践与规范进行自我比较,得出的结论较具理想色彩。在这种研究范式的背后是两种截然有别的逻辑前提:本文的预设则是,指定辩护制度无法脱离辩护制度的系统架构,因而指定辩护律师应以委托辩护律师为角色样板,其理想的辩护效果也应以委托辩护为目标,使之最大程度接近于委托辩护。而既有的研究假定,在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下,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具有无限可能性。
第二,以一个相对封闭的县级司法辖区为样本进行研究,虽然区域较小但其变量更易控制、数据误差较小;既有研究的调查区域虽然更广,但变量更加复杂、不易控制。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相对普适性,笔者选择的调查地区为西部某中心城市的一个郊县D县。无论从经济、社会水平等宏观背景因素,[12]还是案件数量、律师资源等微观外部条件,[13]在全国范围内,D县均居中等水平。故而,对D县状况的考察与分析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同时,调查对象从律师、法官扩展至在押人员、检察官,具体方法上同时采用主观调查(问卷、访谈)和客观调查(统计、档案),力求调查内容更全面、深入、真实。
第三,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既吸收了既有研究的合理成分,又参照了国外相关研究,[14]并结合实际的调查条件而有所拓展。具体而言,笔者将建立一个兼顾客观效果与主观效果,以(客观效果的)过程作用与结果作用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其基本结构如下:(1)客观性指标,指可通过客观数据度量的指标,包括过程作用指标和结果作用指标。 “过程作用”指律师通过辩护权的行使,对诉讼进程的推进作用,具体包括会见、举证、质证的频度、内容、方式,辩护意见提出的频度、意见内容,以及指庭审耗时等情况。“结果作用”指律师辩护对案件审理结果的影响,具体通过辩护意见采纳率、定罪率、无罪判决率与撤诉率、量刑的刑种与量刑幅度等情况表现出来。(2)主观性指标,即诉讼主体的主观评价指标。来自在押人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具体包括对律师辩护作用的总体评价及其原因解释。
2009年9月至11月,课题组在D县进行了调研,收集了如下资料,本文的研究也主要来源于此:
1.阅卷统计数据。课题组查阅了D县法院2007、2008所有一审刑事案卷,共456件、686名被告人,[15]其中,147名被告人有律师辩护,包括指定辩护54人、委托辩护93人。统计信息包括律师辩护/自我辩护与举证、质证、庭审时间、辩护意见、案件处理的关系。
2.问卷数据。课题组于2009年10月向D县所有看守所在押人员、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发放了问卷。其中,接受问卷的在押人员共87人,回收有效问卷85份;律师19人,回收有效问卷18份;法官、检察官分别为7人、4人,回收有效问卷11份。问卷主题涉及律师会见情况、[16]对律师辩护/自我辩护的效果评价及成因解释。
3.访谈笔录。针对统计、问卷发现的问题及需要解释的现象,课题组分别对3名律师、3名检察官、4名法官进行了访谈。
二、过程作用
(一)会见情况
根据刑诉法规定,自被开始,律师可前往看守所与之会见。[17]相比侦查中的会见,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会见不受限制,较为自由。[18]在此前提下,会见频度能够充分反映律师与被告人“顾客关系”的疏密程度,以及及律师辩护的积极性,而会见时的交谈内容则体现着律师的工作方式,直接影响到辩护功能的发挥程度。85份在押人员的有效问卷中,27人有律师辩护,[19]大多数回答了平均会见次数、时间和会见内容的问题。
1.会见频度
调查发现,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在会见次数、个案平均会见时间上基本相当,总体上都不高。由表1、表2可知,指定辩护平均会见1.8次,案均会见19分钟;而委托辩护平均会见2.0次,案均会见18.9分钟。
表1 指定辩护律师案均会见次数[20]
|
|
指定辩护
N1=5人
|
对照组(委托辩护)N2=12
|
|
最多会见次数
|
3
|
4
|
|
最少会见次数
|
1
|
1
|
|
平均会见次数
|
1.8
|
2.0
|
表2 指定辩护律师案均会见时间[21]
|
|
指定辩护
N1=6人
|
对照组(委托辩护)
N2=14
|
|
平均最多(分)
|
30
|
40
|
|
平均最少(分)
|
4
|
9
|
|
案均时间(分)
|
19
|
18.9
|
2.会见内容
根据立法,律师在侦查阶段可通过会见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其会见的功能更是不受限制。考察发现,指定辩护律师虽然比较偏重于通过会见进行辩护准备,但总体上不够积极,这与委托辩护的情形比较接近。
如表3所示,7名指定辩护被告人中,其律师会见时采用了“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咨询”、“说明辩护思路”和“提供辩护建议”等方式的分别有5人、3人、2人和3人,各种方式采用的平均频率较高;而采用了“进行日常生活或感情交流”、“传达亲友问候”的分别只有1人。委托辩护的情形并不相同。在16名委托辩护被告人中,其律师会见时采用“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咨询”、“说明辩护思路”和“提供辩护建议”等方式的分别有6人、4人、5人和5人,其使用频度远不及指定辩护;而采用“进行日常生活或感情交流”、“传达亲友问候”方式上,分别有4人和2人,其频度超过指定辩护,尽管总体频度仍较低。
表3 律师会见内容
N=27人
|
会见内容
|
指定辩护
N1=7人
|
对照组(委托辩护)
N2=20人
|
|
了解案情
|
5
|
6
|
|
向您提供法律咨询
|
3
|
4
|
|
向您说明他的辩护思路
|
2
|
5
|
|
给您提供辩护建议
|
3
|
5
|
|
与您进行日常生活或感情的交流
|
1
|
4
|
|
传达亲友的问候
|
1
|
2
|
|
其他
|
1
|
2
|
|
不明
|
1
|
4
|
(二)举证情况
在刑事审判中,辩护律师有权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出示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证据,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22]一般而言,辩护律师举证数量越多、举证内容越直接、举证方式越具体,辩护的主动性就越强,后续的质证、辩论也会更加充分,也更可能获得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结果。相比其他过程作用指标,举证指标与控辩对抗、案件处理的联系最为密切,也最能体现律师行使辩护权的积极程度。阅卷中,指定辩护律师的举证情况如下:
1.举证频率
考察发现,较之委托辩护,指定辩护律师的举证积极性明显偏低。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举证率很低。54名指定辩护人中,只有7名律师有举证行为,占13.0%,超过80%的律师没有任何举证;与之相比,93名委托辩护人中,有43名律师有举证行为,达46.2%。其二,个案平均举证数量不高。如表4所示,7名有举证行为的指定辩护律师共举证10份,人均举证1.4份,远不足委托辩护的人均举证(2.0份)。如果以全部辩护律师为基数,指定辩护人均举证0.19份,委托辩护则有0.94份。
表4 指定辩护律师人均举证情况
|
|
举证总个数
|
举证人数
/辩护人总数
|
举证频次
(份/人)
|
|
指定辩护
|
10
|
7/54
|
1.4/0.19
|
|
对照组
(委托辩护)
|
87
|
43/93
|
2.0/0.94
|
2.举证内容
较之委托辩护律师,指定辩护律师更倾向于收集量刑情节的证据,其中,虽然略偏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但法定量刑情节证据所占比例也不低。7名指定辩护律师收集的10份证据均为量刑情节的证据,其中,7份证据证明酌定从轻情节,其他3份证据证明法定量刑从轻情节。与之相比,43名委托辩护律师收集的87份证据中,定性证据(无罪或轻罪)证据有16份,占18.4%;量刑情节证据61份,其中,58份为酌定量刑情节证据,法定量刑情节证据仅有3份。
3.举证方式
有限的样本中,相比委托辩护律师,指定辩护律师更倾向于以简便的方式出示证据。如图1所示,在7名辩护律师出示的10份证据中,没有1名采用“全面宣读、出示”或“部分宣读、出示”的方式进行,主要采用“简要说明证据名称+证据内容”的方式(7份证据),其次是“说明证据名称、但无证据内容说明”(3份证据);与之相比,43名委托辩护律师出示的87份证据中,尽管也无人采用“部分宣读、出示”方式,但采用“全面宣读、出示”方式的有28份(占32%),此外,采用“简要说明证据名称+证据内容”的有23份(占26%)、“说明证据名称、但无证据内容说明”的有36份(占42%)。
图1 指定辩护律师举证方式构成
N=97份证据
(三)质证情况
在庭审中,对于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应当进行质证,审判人员应听取辩护人的意见。[23]龙宗智认为,质证是对证据的探究和质疑,包括对证据来源、形式和内容的质疑,而质疑的主要内容和标准是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及证据的合法性(可采性)。质证的意义在于为法庭辩论提供攻击防御之手段。[8]故质证的频率、质证内容的选择,能够直接体现指定辩护活动的积极性与针对性,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控辩对抗的激烈程度。
1.质证频率
对于控方证据,指定辩护人基本不会进行质证。与此相比,委托辩护质证频率高出许多,尽管整体上仍不够积极。54名承担指定辩护的律师中,仅有1名律师提出质证异议,质证率仅为1.9%。对照组中,93名委托辩护律师中有29人进行质证,质证率为31.2%,远远高出前者。这表明,相比委托辩护律师,指定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质证态度显得相当消极。
2.质证内容
进一步分析,仅有的一名提出质证异议的指定辩护律师,其质证焦点在于证据客观性方面。由于样本太少,无法就指定辩护律师更倾向于哪方面的质证内容作出结论。与之相比,如表5所示,29名委托辩护律师提出88次异议,其中,50%集中在证据客观性方面,证据证明力和证据资格问题各占23.9%和26.1%。
表5 指定辩护律师质证内容构成
单位: 份(%)
|
异议内容
辩护类型
|
证据
客观性
|
证据证明力(相关性)
|
证据
资格
|
总计
|
|
指定 N1=1人
|
2
|
0
|
0
|
2(100)
|
|
委托 N2=29人
|
44(50.0)
|
21(23.9)
|
23(26.1)
|
88(100)
|
(四)辩护意见状况
辩护意见主要集中在法庭辩论阶段,[24]尤其体现在辩护词中。它包括对证据、事实的认识,以及对案件性质、情节等法律适用问题的看法,是辩护律师与公诉人相互辩论的基础。功能上,辩护意见与公诉意见共同构成庭审调查与法庭裁判之间的联结纽带。辩护意见提出的频度及其内容,既能表现律师对案件的综合认识和判断,也能反映法庭辩护阶段的控辩对抗程度。
1.辩护意见提出的频度
有效的样本案件中,指定辩护律师都会提出辩护意见,个案意见的频率不低,但相比委托辩护仍有所不如。54起指定辩护案件,53名被告人的案件庭审笔录记载了律师提出辩护意见的情况,有效样本为53件。在有效样本案件中,指定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最少2个,最多5个,平均3.4个。而在93起委托辩护案件中,有效样本为87件,律师提出辩护意见的最少0件,最多11件,平均4.4个。
表6 指定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频度
单位:件
|
|
最多
|
最少
|
平均
|
|
指定辩护N=53人
|
5
|
2
|
3.4
|
|
对照组(委托辩护)N=87人
|
11
|
0
|
4.4
|
2.辩护意见内容
从内容看,指定辩护意见主要集中在量刑情节方面,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定性辩护很少,程序性辩护没有。与之相比,委托辩护中法定量刑情节的辩护比例更低、定性辩护所占比例较高。如图2-1所示,在所有辩护意见中,量刑情节的辩护占96%,其中,酌定情节占63%,法定情节占33%。定性辩护仅占4%,其中,“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占3%,“基本事实成立,但依法不够成犯罪”占1%,无律师就“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犯罪事实”、“基本事实成立,但构成轻罪”及“取证违法”提出意见。对照组方面,如图2-2所示,量刑情节辩护占85%,其中,酌定情节辩护占67%,而法定情节辩护只有18%;定性辩护约占18%,其中,“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占8%,其次是“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犯罪事实”(4%)和“基本事实成立,但依法不够成犯罪”(2%),而“基本事实成立,但构成轻罪”占 1%。
图2 指定辩护意见构成情况
图2-1 指定辩护意见构成
图2-2 对照组:委托辩护意见构成
(五)庭审效率状况
律师在庭审中的活动包括向被告人发问、质证、举证及参加庭审辩论,上述活动会耗费一定时间。理论上,辩护活动的积极程度与庭审效率应成反比关系,即律师表现越积极,则庭审耗时越长,庭审效率越低。在此,可以指控严重性、案件复杂性为依据,分别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两类案件中对指定辩护案件的庭审效率进行考察。[25]
考察发现,简易程序案件中,指定辩护案件的庭审效率与委托辩护相当,而在普通程序案件中,指定辩护案件的庭审效率则明显高于委托辩护案件。如表7所示,在简易程序案件中,指定辩护案件平均庭审耗时45分钟,只比委托辩护案件多1分钟,差别不显著。而在普通程序案件中,指定辩护案件的平均庭审时间为96.1分钟,明显不及委托辩护案件的112分钟,两者之差为15.9分钟。这表明,普通程序的庭审中,指定辩护律师的积极程度不如委托辩护律师。
表7 指定辩护案件的庭审效率
|
程序
类型
|
庭审时间(分钟)
辩护类型(件)
|
最长/最短
|
平均
|
平均时
间量差
|
量差比
|
|
简易
程序
|
指定辩护 N= 4
|
50/30
|
45
|
+1.1
|
1.03:1
|
|
委托辩护 N=9
|
110/30
|
43.9
|
|
普通
程序
|
指定辩护 N=49
|
150/40
|
96.1
|
-15.9
|
0.86:1
|
|
委托辩护 N= 84
|
295/40
|
112.0
|
三、结果作用
(一)辩护意见采纳率
辩护意见的采纳情况最直接地反映了律师辩护效果。D县的审判实践中,辩护意见采纳情况主要体现在判决书的说理内容之中,故据此可以统计、分析采纳率。
考察发现,总体上,指定辩护意见采纳率为中等偏上,与委托辩护相比,量刑辩护的采纳率稍高,而定性辩护方面则有所不如。如图3所示,指定辩护意见中,就“法定从宽”和“酌定从宽”情节作出的辩护意见采纳率分别为73%和82%,略高于委托辩护辩护的对应情形(58%和74%)。指定辩护在“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上的意见采纳率也略高于委托辩护,前者为67%,后者为55%。而在“基本事实成立,但不够成犯罪”上的意见采纳率为零,远不及委托辩护(49%)。考虑到指定辩护律师很少提出定性辩护意见,在此方面的比较没有明显的实际意义。
图3 指定辩护意见的采纳率
单位:%
(二)定罪量刑情况
定罪、量刑结果取决于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与具体的法律运用,而法官的认识与判断不仅来源于案卷、公诉意见,还会受到辩护律师的举证、质证及辩护意见的影响。因此,定罪、量刑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律师辩护的成效。
1.定罪情况
分析发现,相比委托辩护案件,指定辩护案件的被告人更可能被判有罪。53名有指定辩护律师的被告人,均被判有罪。不过,只有4起案件的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其中,3起的辩护意见为“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但未得到采纳。在一起“贩卖、”的审判中,4名被告人中有1名未成年被告人的指定辩护人提出“制造、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法院部分采纳,最终,法院就“贩卖毒品罪”一案作出无罪判决,尽管并未影响到案件整体的定罪效果。
与指定辩护案件相比,委托辩护案件在定性方面似乎更可能取得有利于被告人的结果。93名委托辩护的被告人中,有9名被告人被作出全部或部分无罪处理。“全部无罪处理”是指检察机关撤诉,有4名被告人属此情形。“部分无罪处理”是指,公诉机关指控两个或两个以上罪名及相应的犯罪事实,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不构成其中一项罪名,但其余指控成立,有5名被告人属此情形。进一步分析无罪处理的情形,应都与律师的积极辩护有关:(1)撤诉案件。4起撤诉案件中,有3起为故意伤害(轻伤)的自诉案件,另1起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公诉案件。这4起案件中,辩护律师提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意见,经控、辩、审三方交换意见,自诉人或公诉机关认为难以胜诉,最终撤回起诉。(2)部分无罪处理案件。在5起作出部分无罪处理的案件中,各有2名辩护律师提出“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或者“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犯罪事实”的辩护意见,另1名律师提出“基本事实成立,但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均得到法庭采纳。
2.量刑情况
从辩护意见的提出情况看,绝大多数都与量刑情节有关,而且从形式上,大部分也得到采纳。由此可以初步认为,指定辩护对于量刑结果具有积极作用。但其作用程度如何,不同案件所受影响大小怎样,还需要与委托辩护进行对照比较。通过在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框架内进行比较,并未得出指控相当的案件中,指定辩护对量刑结果的积极影响优于委托辩护的结论。
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指定辩护的被告人获得的量刑结果似乎不及委托辩护。如图4所示,适用简易程序的指定辩护、委托辩护案件分别有4件、9件。其中,指定辩护中3件判处实刑,有1件判处;而委托辩护的9起案件中,有7件判处缓刑,缓刑率大大超过指定辩护。实践中,除了无罪判决、撤诉、定罪免处,缓刑被普遍视为对被告人最有利的量刑方式。据此可以认为,指控较轻并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指定辩护的量刑效果不如委托辩护。但由于样本过少,上述结论不具有确定性。
图4 简易程序中指定辩护案件的量刑结果
单位:%
有意思的是,普通程序中的比较却似乎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如图5所示,49名指定辩护的被告人中,缓刑率为61%,超过委托辩护19%。据此是否可以认为获得指定辩护的被告人相比委托辩护更可能得到较轻刑罚?显然不能,因为上述比较尽管考虑了指控严重性这一因素,却没有考虑被告人的年龄这一重要变量。根据现行,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第17条)。而在适用普通程序的49名指定辩护被告人中,有39人为未成年人,占79.6%。换言之,大多数指定辩护的被告人都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据此,指定辩护的缓刑率之所以超过委托辩护19%,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被告人属于未成年人”这一因素。因此,在整体上,普通程序中的比较同样未得出指定辩护的量刑结果优于委托辩护的结论。
图5 普通程序中指定辩护案件的量刑结果
单位:%
四、诉讼主体的评价
(一)顾客关系——被告人的评价
在押人员的问卷评价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态度,其二则直接涉及律师辩护的成效。有限的问卷发现,指定辩护的在押人员对律师态度的总体评价较高,明显超过委托辩护的在押人员;而在辩护效果方面,认为律师作用至关重要的很少,与委托辩护的情况相似。
对于“你的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表现(态度)如何?”一问,如表8所示,7名指定辩护的在押人员中,有4人选择“很积极很努力”,认为“一般”和“比较消极”的各1人,另有1人未作回答。与之比较,20名委托辩护的被告人中,认为律师“很积极很努力”的仅有3人。
表8 问卷:“你的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表现(态度)如何”
单位:人
|
会见内容
|
指定辩护
N1=7人
|
对照组(委托辩护)
N2=20人
|
|
很积极很努力
|
4
|
3
|
|
一般
|
1
|
5
|
|
比较消极
|
1
|
3
|
|
说不清楚
|
0
|
2
|
|
未选择
|
1
|
7
|
对于“你的辩护律师对案件审判结果是否有影响”一问,7名指定辩护的被告人中,认为影响的有3人,其中,认为“有关键影响”的只有1人;认为没有影响的也有3人。此外,还有1人称“说不清”。对照组的情况较为相似,委托辩护的20名被告人中,认为律师“有关键影响”的也仅3人。
表9 问卷:“你的辩护律师对案件审判结果是否有影响”
|
会见内容
|
指定辩护
|
对照组(委托辩护)
|
|
有关键影响
|
1
|
3
|
|
有一些影响
|
2
|
3
|
|
基本没有影响
|
1
|
1
|
|
完全没有影响
|
2
|
3
|
|
说不清
|
1
|
5
|
|
未选择
|
0
|
5
|
|
总计
|
7
|
20
|
(二)司法人员的评价
司法人员的问卷情况包括三部分:其一,相比委托辩护,指定辩护的总体效果如何;其二,对指定辩护总体效果相对较好/较差的原因进行解释;其三,就律师辩护(包括指定辩护)对审判结果的影响力进行评价。问卷结果显示:所有司法人员一致认为,指定辩护效果不如委托辩护,指定辩护律师的专业水平相对较低是其主要原因;而在整体上,律师辩护(包括指定辩护)对定性、量刑的影响程度都不大,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公正审判方面。
对于“你认为哪种辩护方式效果更好”一问,11名受访司法人员均认为指定辩护不如委托辩护,其中,更有2名司法人员认为指定辩护甚至不如公民辩护。针对这一结果,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你认为指定辩护效果不如委托辩护,原因是什么?”对此,有7名司法人员认为指定辩护律师在专业性和法律知识方面不如委托辩护律师,有2人认为委托辩护律师收了钱、比指定辩护律师更加卖力,另有2人认为指定辩护律师在建立与当事人的信任关系方面不如委托辩护。
在律师辩护(包括指定辩护)的整体效果方面,如表11名受访人员中,超过一半(7人)认为律师辩护“给被告人提供公平审判的机会”,其次是“为司法机关与被告人之间提供沟通途径”、“影响证据、事实的认定”(分别有5人),而“影响量刑的轻重”、“影响刑法上的定性”偏少(分别只有4人、3人)。
表10 问卷:“你认为律师辩护对刑事审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N=11人
|
选项
|
选择人数
|
|
给被告人提供公平审判的机会
|
7
|
|
为司法机关与被告人之间提供沟通途径
|
5
|
|
影响证据、事实的认定
|
5
|
|
影响量刑的轻重
|
4
|
|
影响刑法上的定性
|
3
|
五、结论与探讨
(一)“作用阶梯”现象
从80年代以来,有关公设律师[26]的辩护效果问题在美国一直倍受关注。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揭示出,公设辩护的效果在总体上不如委托辩护,尚未达到“合理的有效性援助”的要求。麦高伟等人以辩护动议为指标进行的早期研究发现,公设辩护人提出的辩护动议明显少于委托辩护人。[9] Steven K. Smith 和Carol J. De Frances的研究中,公设辩护人在逮捕后一周内会见被告人的只有47%,低于委托辩护人22个百分点。[10]Roger A. Hanson等人考察了诉讼周期、辩诉交易率、定罪率和撤案率等现象,结果发现,公设辩护人案件的诉讼周期平均为103天,远低于委托辩护人的案件(160天);辩诉交易率为95%,略高于委托辩护(91%);定罪率则与委托辩护相同,均为88%;撤案率为9%,低于委托辩护(13%)。[11]Morris B. Hoffman等人以量刑幅度为指标进行的研究中,当不考虑指控严重性的因素,公设辩护较之委托辩护的刑罚高出5年,而当控制了指控严重性这一变量之后,公设辩护案件的刑罚仍然超出委托辩护3年。[12]
尽管有不同的制度背景与现实条件,但笔者通过考察发现,D县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竟与美国公设辩护的状况大体相似,这可概括为“作用阶梯”现象。具体而言,指定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尽管明显优于被告人的自我辩护,但与委托辩护律师相比,却又存在一定差距,某些方面甚至差距较大,从而表现为“作用阶梯”现象。在D县,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的差距主要体现在:
第一,指定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表现明显不如委托辩护,后者相对积极。如果以庭审效率为考察对象,普通程序中指定辩护比委托辩护案件的庭审时间明显更短,而这种时间差距与辩护律师在庭审中表现的积极程度具有相关性。具体而言,指定辩护律师的举证频率远低于委托辩护律师,偏向于以更简单的方式举证;针对控方举证,指定辩护律师基本不参与质证,从而与委托辩护律师一定比例的质证率形成鲜明对比;在辩护意见发表频率方面,指定辩护律师虽然表现不弱,但与委托辩护律师相比仍有不如。不仅如此,指定辩护律师举证和发表辩护意见的内容都立足于进行量刑辩护,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的辩护,相比而言,委托辩护律师在定性辩护方面作用较大。
第二,指定辩护律师在案件定性方面作用不大,较之委托辩护略有不如。在涉及案件定性问题上,指定辩护律师不仅很少提出辩护意见,已有的辩护意见也很难得到法院支持。就判决结果而论,样本案件中,指定辩护的案件都产生有罪判决,而委托辩护的案件有一定比例得到无罪处理(撤诉和无罪判决)。仔细分析可发现,案件的无罪处理结果与委托辩护律师的积极辩护密切相关。
第三,从司法人员角度,指定辩护律师发挥的整体作用不及委托辩护律师。司法人员不仅作出指定辩护效果不如委托辩护的判断,而且还指出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即指定辩护律师的专业性不如委托辩护律师。在D县,承担指定辩护业务的是在县法律援助中心承担援助义务的专职律师,他们通常不从事委托辩护工作。因此,司法人员评价所指的是援助律师的专业性不如社会律师。由于司法人员立场中立,其评价的客观可信度较高。尽管接受指定辩护的被告人对自己的律师评价不低,但笔者宁愿相信,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指定辩护是“免费午餐”,接受援助的被告人原本的期望值就不高。
总而言之,在D县,指定辩护律师发挥的作用既与委托辩护有所差距,而从其具体表现看,也未达到“客观职守型辩护”要求,而距“合理有效性援助”更是相去甚远。
(二)何以形成“作用阶梯”?
对于公设辩护效果不尽如意的问题,有美国学者将其归咎于“不充分的补偿”、“政府在提供支持性服务和培训方面的失败”、“公设辩护人职业独立性的不足”、“监督与质量控制标准的欠缺”及“系统化公设辩护体制的缺乏”。[13]另有学者则指出,公设辩护人案件负担过重是问题之根由。[27]就我国的指定辩护作用问题,案件负担过重、人员培养失败等归责理由并不适合,[28]相对而言,指定辩护律师介入时间、资金保障和质量管理的因素也许影响更大。具体表现在:
其一,指定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时间过晚。按照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29]但是,即使法院刑庭在安排指定辩护时遵守了上述时间限制,也并不意味着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会及时受理案件。据访,D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受案件后,在指定律师办理之前还会有2-3天受理审查,留给律师准备辩护的时间只有7-8天。个别情况下,律师甚至在开庭前1-2天才接受案件。由于时间紧迫,律师的辩护准备也较为匆忙、粗疏,会见走过场,即使发现证据线索也无力调查取证,而不得不主要借助于阅卷发现有利于被告人的信息。
其二,刑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充分。2006年,我国法律援助的人均经费不足0.3元。[30]而在D县法律援助中心,从2005-2009年,除工资外每年由县财政拨款5万元作为业务经费,无任何社会捐助等其他方式的经费来源,全县人均援助经费仅有0.1元。有限的经费应用于三方面支出:办案经费,办案补贴和日常办公。然而,对D县法律援助中心的调查发现,已有经费仅基本满足日常办公所需,而办案补贴极少、案件调查方面的支出更是无力报销。以办案补贴为例,根据S省《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在本市区内、本县(市)内办案的,刑事案件每件补贴200—800元。实际上,D县援助中心采用了最低补贴标准,即每年补贴200元。与之相比,根据S省《律师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的规定,委托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的收费标准为3000—30000元。而在笔者对D县律师的问卷中,有14人在问卷中填写了自己收取的个案平均代理费用,最高为8000元,最低为1000元,案均收费3071元,远远高于援助补贴标准。进一步,经费保障的不足带来两方面后果:一方面,由于办案补贴极低,指定辩护律师普遍缺乏责任感与积极性,办案过程多属应付;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专门的办案经费,即使确需调查取证,辩护律师也通常不得不放弃。
其三,指定辩护质量监控机制偏于形式化。委托辩护的质量控制机制具有协商性特征。[31]与此不同,对于指定辩护,政府方面采用“卷宗式”质量控制机制,即通过对辩护案卷的管理和审查来监督办案质量。在D县,每名援助律师办理案件都要填写司法部制发了一整套格式文书,格式文书涵盖了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法律援助工作环节,包括法律援助申请表、审查决定书、指派律师函等等;除此之外,还要求将阅卷笔录、会见笔录、庭审笔录、辩护词、判决书附卷。援助中心对个案的监督主要是在案件办理完毕以后申请补贴时对交回的案卷材料进行书面审理,只要具备上述文书和材料就可结案;年终考核时,上级援助管理机构也会就此进行规范化审查,但审查的重点仍然是上述文书和材料是否已经齐备。有论者称这种监督机制为“形式审查为主,兼顾实质审查”。[14]这种审查的对象是案卷,其质量导向是“办案规范化”,而基本不涉及具体的辩护策略、辩护方式和辩护效果。客观上,形式化的质量监督机制确实能够保证援助律师能够按部就班地履行辩护职能,从而大体上符合“客观职守型援助”的底限标准,但也仅此而已。与“合理的有效性援助”目标则相去甚远。
衡量公正审判是否实现的标准并不仅仅是被告人是否获得律师辩护,还涉及辩护律师是否尽最大可能为被告人提供帮助。本文的研究发现,受制于各种外部、内部因素,指定辩护的作用较为有限,而进一步加强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提高其辩护效果,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内、外因素的调整与变化。此外,确立适当的改革目标也是不可或缺。在我看来,指定辩护制度的改革应确立两个目标:以达到委托辩护作用为近期目标,而以接近有效性辩护为远期目标。具体的改革与实践之中,这两个目标难以截然分开。这是因为,在改进指定辩护方式、提高辩护效果,基本达到委托辩护水平的同时,也意味着与有效性辩护目标的距离缩短。但是,考虑到即使是委托辩护,其实际效果也与有效性辩护尚有较大差距,因此,这种目标层次的设定也有其意义。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Court-Appointed Counsels:
in Comparison with Hired Lawyers
Abstract: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rt-appointed lawyers, the current law adopts a standard of objective diligence, but a higher requirement shall be 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In the sample jurisdiction of D County, there is a obvious gap 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rt-appointed counsels and hired lawyers. From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hired lawyers are more active in court than appointed lawyers, and are more capable in obtaining better results for the defendants. When evaluated by other legal professionals, appointed lawyers often received lower assessment. Major reasons for such differences include late involvement of appointed counsels, budgetary shortage, and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Improvement of the function of court-appointed counsels also relies on those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although an appropriate goal is necessary.
Key Words: Court-appointed representation, Hired representation, Objective diligent appointed-representation, Reasonable effective appointed-representation,
[1] Barbara Allen Babcock. Inventing the Public Defender [J].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2006,(43): 1268.
[2] John H. Cayce. Criminal Law—Assistance of Counsel—“ Reasonably effective Assistance” Standard is Applicable to Both Retained and Apponted Counsel without Distinction [J]. 13 Saint Mary's Law Journal, 1981, (13):166-168.
[3] 蒋建峰,郭婕. 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J]. 中国司法,2004,(3):81.
[4] 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 2008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 [EB/OL].(2009-04-07)[2010-07-08].http://www.moj.gov.cn/flyzs/2009-04/07/content_1066224.htm.
[5] 陈瑞华.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7-340.
[6]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法律援助部调研组.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调研报告[J].中国司法,2004,(12):52.
[7] 孙洪坤.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实证分析——对淮北市法律援助中心、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5):103-104.
[8] 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8.
[9] Michael McConville & Chester L. Mirsky. Criminal Defense of the Poor in New York City[J]. N.Y.U. Rev.L. &Soc. , 1986-87,(15):582.
[10] Steven K. Smith & Carol J. De Frances. U.S. Dep't of Justice[J].NCJ, Indigent Defense, 1996:158909.
[11] Roger A. Hanson et al. Indigent Defenders: Get the Job Done and Done Well[R].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1992.
[12] Morris B. Hoffman, Paul H. Rubin & Joanna M. Shepherd. An Emprical Study of Public Defender Effectiveness : Self-selection by the “Marginally Inigent ”[J].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2005: 223.
[13] Thomas E. Daniels. Gideon’s Hollow Promise – How Appointed Counsel are Prevented from Fulling their Role in the Criminal System[J]. Michigan Bar Journal, 1992,(71):136.
[14] 蒋建峰. 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及质量控制考察报告[J]. 中国法律援助,2006,(1):38-40.
* 本文系笔者主持之司法部2008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刑事一审程序中辩护律师作用之实证研究”(编号08SFB3018)最终成果之组成部分。
[1] 以英、美为例。在英国,直到《1903年贫穷囚犯辩护法》(the Poor Prisoners’ Defence Act of 1903),因严重犯罪而被送交审判且没有足够财力的被告人,才能获得免费的法律代理;而不考虑案件严重性,只要被告人财力有限,就能获得免费辩护的原则直至《1949年法律咨询与援助法》(Legal Advice and Assistance Act 1949)才加以确立。参见[英]李•布里奇斯.律师代理与法律援助的权利.吴丹红,译[C]//[英]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8. 在美国,最高法院最初在鲍威尔案(Powell v. Alabama,1932)中确定,案件的被告人应当得到指定律师的帮助,进而,又通过策尔普斯特案(Johnson v. Zerbst,1938)明确,在联邦刑事审判中,所有贫困的被告人都有权获得政府资金指定的律师帮助的权利。直至1963年的吉狄恩案(Gigeon v. Wainright,1963),最高法院才通过适用正当程序条款,使指定辩护原则普适于各州。参见[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魏晓娜,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1-56.
[3] Powell v. Alabama, 287 U.S.45, 1932.
[4] McMann v. Richardson, 397 U.S.759, 1970.
[5] 570 S.W.2d 941,Tex. Crim. App., 1978.
[6] Cuyler v. Sullivan, 100 S. Ct. 1708, 1716, 64 L. Ed. 2d 333, 344, 1980.
[7] 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7条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8]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
[9]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10]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全文数据库》,其中百分比情况系笔者根据案件数量计算所得。
[11] 相关文献可参见马明亮,张星水.中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实证分析[C]//陈瑞华.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1-171;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法律援助部调研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调研报告[J].中国司法.2004,(12):52-53;孙洪坤.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实证分析——对淮北市法律援助中心、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5):103-104.
[12] D县距S省省会48公里,人口51万余人,面积1321平方公里。2008年度,D县人均GDP为15135元,而该年度S省、全国的相应数据为15342元和22698元。全国数据来源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9》,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9/indexch.htm。
[13] 就一审刑事案件数量和律师资源而言,2008年D县人民法院审结227件337名被告人,每10万人44.5件;在D县执业的律师共19人,每10万人中有3.7名律师。而同期全国法院的一审刑事案件总数为768130件,每10万人57.8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全国法院审结刑事一审案件情况. [EB/OL].(2010-02-21)[2010-07-08].
http://www.court.gov.cn/qwfb/sfsj/201002/t20100221_1421.htm;全国有律师14万人,每10万人中有律师10.5人,参见宋伟.我国执业律师总数达14万人[N].人民日报.2008-10-26.
[14] 相关文献参见 Michael McConville & Chester L. Mirsky. Criminal Defense of the Poor in New York City[J]. N.Y.U. Rev.L. &Soc. Change, 1986-87(15) :581; Roger A. Hanson et al. Indigent Defenders: Get the Job Done and Done Well.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1992; Steven K. Smith & Carol J. De Frances. U.S. Dep't of Justice[J].NCJ, Indigent Defense, 1996:158909; Morris B. Hoffman, Paul H. Rubin & Joanna M. Shepherd. An Emprical Study of Public Defender Effectiveness : Self-selection by the “Marginally Inigent ”[J].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2005:223. 其中,McConville的指标为律师提出的审判动议数量,Hansonetal采用的指标体系包括诉讼周期、辩诉交易率、定罪率、撤案率,Steven的指标为最早会见时间,而Morris等人则采用了量刑严重性标准。
[15] 据D县法院司法统计数据显示,2007、2008年审结的刑事案件数实际为460件、685名被告人,但由于卷宗外借原因,有18件26名被告人的案卷资料无法统计分析。故统计分析对象只有442件、659名被告人。
[16] 之所以对会见情况采用问卷方式考察,是因为法院的案卷材料无法反映律师会见的情况。相对而言,对被告人的问卷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了解相关信息。由于调研时间是2009年9-10月,彼时已无法对2007、2008年法院审理案件的在押人员进行问卷。因此,这项问卷调查与案卷分析结果无法完全对应。尽管如此,由于调查区域的一致性、调查对象的相似性、调查时间的相继性,问卷调查情况基本能与案卷分析形成有效衔接。
[18]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之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据上规定,律师在侦查中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主要会受到“安排程序”及“在场监视”的制约,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见效果。而在审判阶段,既不存在安排会见问题,也不存在司法人员在场监视问题,会见自由权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
[20] 指定辩护中会见次数不明者2人,委托辩护中会见次数不明者8人。
[21] 指定辩护中会见次数不明者1人,委托辩护中会见次数不明者6人。
[24] 我国刑诉法规定,经审判长许可,辩护人可以对证据和案情发表意见。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60条。
[25] 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分类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被告人可能判处刑罚的严重程度,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以下刑罚的案件,而普通程序主要适用于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其二是被告人是否认罪,在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中,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不认罪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因此,以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划分为基准,在适用同一种程序的案件中进行庭审时间的比较分析大致符合“同类比较”的原则。
[26] 在美国,公设辩护人是指由政府付酬,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专职律师。它是基于任何被告人(包括贫困的被告人)都平等地享有律师辩护的宪法权利而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参见Barbara Allen Babcock. Inventing the Public Defende[J].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2006, (43):1267.从严格意义上,我国尚未设立这一制度,但既已存在的指定辩护制度大体上具备了公设辩护制度的雏形。因此,两类制度在概念上基本对应。
[27] 例如,全美首席公设辩护人事务会(ACCD)建议的标准为,公设辩护人每年办案不超过150起重罪案件或400起轻罪案件,但在洛杉矶公设辩护人办公室,近年来办理重罪案件的公设辩护人人均每年超过180件,办理轻罪案件的人均超过1200件。参见Nancy Albert-Goldberg. Los Angeles County Public Defender Office in Perspective[J]. California Western Law Review, 2009, (45):451-452.
[28] 在我国,指定辩护率很低,而可供指定的律师数量不少,指定辩护人的案件负担并不大。在D县,2007、2008年的指定辩护案件只有54件,而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有3人,人均每年仅办理9件,每月不足1件。就全国范围而言,2006年的数据显示,当年法律援助机构执业律师5006人,指定辩护案件总量96762件,由此计算,每名援助律师平均承办案件约19件。考虑到有大约一半的援助案件由社会律师办理,专职援助律师平均承办的案件实际上可能不足10件。相关数据参见丛卉. 2006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J].中国司法,2007,(5):103-105. 在人员培养方面,专职从事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的来源与社会律师没有区别,都要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而在继续培训方面,众所周知,专职律师和社会律师每年都要接受地方律协一定课时的培训方能注册。故从人员培养角度,很难解释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的效果差异。
[30] 2006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收入总额为37029.78万元,而当年总人口已超过13亿。参见丛卉. 2006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J].中国司法,2007,(5):103.
[31] 其协商性特征表现在,委托人与辩护律师就工作责任及其目标进行书面或口头约定,并据此给付费用。这种调控机制有助于促进律师辩护的积极性,促使其穷尽各种可能的途径以争取有利的案件处理结果。
声明:本网部分内容系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
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本站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应用建议。本站拥有对此声明的最终解释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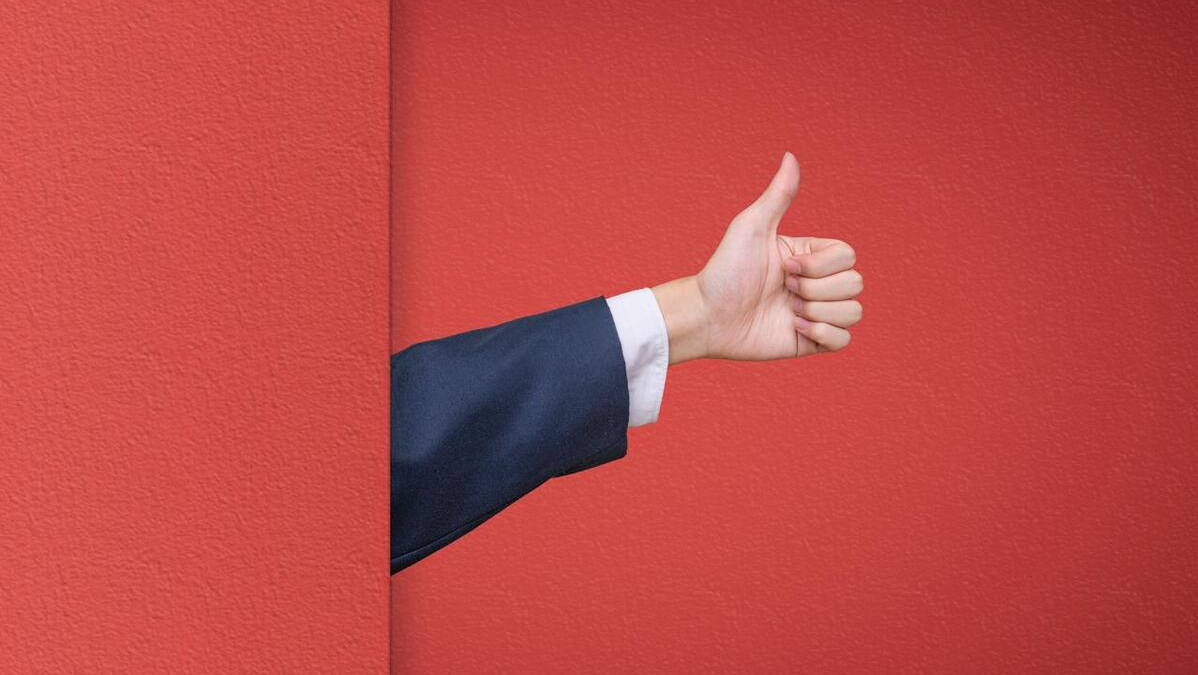



发表评论